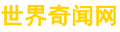黑暗史诗2中文版(暗黑2重制版:颠覆传奇的史诗操作,2个半小时从零开荒通关全难度)
黑暗史诗2中文版文章列表:
- 1、暗黑2重制版:颠覆传奇的史诗操作,2个半小时从零开荒通关全难度
- 2、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简体中文如何设置图文教程
- 3、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公布 画质全面更新,年内上线
- 4、一场团战损失百万?盘点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PK端游,你玩过几个?
- 5、专访|席慕蓉:我给记忆命名,从此有了归属与顾盼
暗黑2重制版:颠覆传奇的史诗操作,2个半小时从零开荒通关全难度
说游戏,聊故事,大家好,我是小翎~
随着暗黑2重制版的面市,时隔十余年未曾有过改动的暗黑2也进入了全新的时代,终于迎来了2.4版本补丁,全职业技能大幅度改动,诸多装备也有了变化。让这款经典的游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就在版本更新之后,暗黑2限制级玩法——从零开荒至地狱通关(以下简称速通)的记录再度被刷新。而且刷新此玩法的玩家,就是我们国服的一位大神。此篇,小编就和大家说说,这颠覆传奇的史诗操作吧~
暗黑2重制版:颠覆传奇的史诗操作,2个半小时从零开荒通关全难度
01
刷新记录的国服玩家——2nan
在暗黑2未更新的十余年中,各路大神开始挑战起限制流玩法。虽然暗黑2本身的难度就极高,但在大神级玩家眼中,原版的难度并不能满足他们。因此就诞生了裸装通关、最低等级击杀隐藏boss、各种限制速通等等。
其中钟爱速通的玩家最多,就在重制版开启之初,一些玩家还自掏腰包组织过速通大赛。本篇的主角——2nan也曾参与其中,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而在2.4版本更新之后,这位玩家更是在直播中打出了刷新世界纪录的成绩,将之前的2小时42分,刷新至2小时35分!
一个没有任何遗产的角色,仅用两个半小时就彻底通关这款游戏,当真可怕至极!
02
使用全新流派——冰火法
2个半小时,对于小编这种手残玩家,只够走到普通难度的第三幕,在热带雨林里被小矮人揍得七荤八素。确实令小编惊叹不已,其操作和对游戏的理解已是顶级。
与此同时,这次世界纪录的刷新,也为大家印证了一件事。2nan在此次速通中,并没有使用传统的纯冰法,而是用冰火法的玩法,以暴风雪作为主力输出,也点出了九头海蛇作为弥补伤害。
包括小编在内的不少玩家,之前曾极力推荐过冰火法的开荒流派。经过2nan大神的证实,2.4版本之后,冰火法的开荒实力,确实较纯冰更加强力。
虽然我们并没有大神那般的神级操作,但在冲天梯开荒之时,也可以考虑点出九头海蛇,使用冰火流开荒通关。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也想要快速开荒的玩家,也可以试着学一些小技巧。比如卡五小队,逆时针寻路等。
而使用的符文之语,包括隐秘、知识、精神,依旧是开荒的利器,大家可以作为参考使用哦~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需要多久才能通关这款游戏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感谢各位读者的阅读,也请顺手点个赞和关注,原创码字不易,万分感谢。
小编将持续带来新版本的浅析和玩法,最后,祝愿所有读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能欧气满满,财运滚滚,健康平安,开心快乐每一天~
举报/反馈
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简体中文如何设置图文教程
《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发售后热度暴涨,不仅当晚服务器被挤爆,次日媒体平台和社交平台的讨论度更是离谱,这是百度指数增长线:
很多玩家在战网平台购买游戏后,找不到简体中文的设置选项,但是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有这个模式,都很好奇是怎么操作的,其实操作很简单:
先启动并登录战网国际服。桌面状态下,运行(win r)输入regedit。
打开如下路径:计算机HKEY_USERSS-1-5-21-3188958727-4197864613-4173097096-1001SOFTWAREBlizzard EntertainmentBattle.netLaunch OptionsOSI
双击LOCALE,将数值数据改成zhCN。
更改完后,从《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的游戏所在文件夹里,直接打开D2R.exe启动游戏,不要从战网国际服启动,不然会汉化失败。
简体中文界面如下:
战网国际服可以直接用奇游客户端的引导提示去下载,另外奇游也支持游戏的满速下载提速和联机加速,保证游戏体验:
《暗黑破坏神II:狱火重生》(英语:Diablo II: Resurrected)是《暗黑破坏神II》及其资料片《暗黑破坏神II:毁灭之王》的重制版,研发商为暴雪娱乐,Vicarious Visions参与开发,支持4K(2160p)超高清分辨率,游戏音效通过杜比7.1环绕声重制,覆盖Windows、PlayStation4、PlayStation5、Xbox Series X和Xbox Series S、Xbox One以及任天堂Switch等平台。游戏发售后的口碑都非常不错,感兴趣的玩家们赶紧去体验吧!
以上是关于《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简体中文如何设置图文教程的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公布 画质全面更新,年内上线
在今天早上的暴雪线上嘉年华开幕活动中,暴雪公布了万众期待的《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该作将包括所有来自《暗黑破坏神2》及其《毁灭之王》的游戏内容。游戏预计2021年上线,登陆PC/PS5/PS4/XBOXS X|S/Switch多平台。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该作的预告片吧。
游戏预告:
重制版画质—怪物、英雄、物品和法术等各种内容全面更新。
透过五个章节所诉说的史诗级故事。
经典游戏玩法—玩家所熟悉的那个超人气《暗黑破坏神2》经典重现。
新增 Battle.net 支援功能。
预计支援跨平台进度功能—不论你透过哪个平台进行游戏,都可以接续先前的游戏进度。
视频画面:
一场团战损失百万?盘点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PK端游,你玩过几个?
有句话说:“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句话在游戏中也同样如此,相比于跟程序写好的NPC战斗,跟真实存在的玩家角色进行战斗更加刺激、有趣,也就是大家常说的PK。
PK玩法的存在也是网游这种类型游戏经久不衰的原因。因此也有不少网游选择专注于PK玩法,本篇文章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比较经典的PK网游。
《热血传奇》
既然说到了PK,那么在国内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热血传奇》肯定是无法绕过去的。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热血传奇》算得上是游戏启蒙之作。这款在韩国不温不火的游戏,在被盛大陈天桥引进国内之后,就犹如凤凰涅槃一般,从草鸡变凤凰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游戏。
游戏中拥有经典的战士、魔法师和道士三种职业,玩家通过刷怪打装备来提升自己的人物。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游戏玩家中十名里有九名正在玩《热血传奇》,而剩下的一个也正在被其他传奇玩家安利来玩的途中。在那个互联网都刚刚起步的年代,《热血传奇》1.1版本“三英传说”开始公测,在不到一周内就造就了万人同时在线的壮举。
不过如果要说《热血传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玩法,那毫无以为是全地图无所谓不在的PK,以及团队PK玩法的“沙巴克城战”。PK中被杀会随机掉落装备的设定,所带来的刺激让不少玩家沉迷其中,也正式借由《热血传奇》之手,把PK玩法普及到全国玩家,甚至后来还出现了不少模仿者。
《决战轩辕》
《决战轩辕》是由众川网络研发,珠海心游科技代理的复古经典2D硬派PK网游。游戏在职业体系的设定上就参考了《热血传奇》,拥有战士、法师以及符师三个标准的经典职业,并且在三大职业的基础上,为每个职业设计了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天赋系统。
通过自由切换,实现技能和玩法的多重选择。比如符师,可以选择召唤流或是治疗流;而战士则可以选择攻防兼备的刀盾流或是双手双持的斧战流。法师则会根据元素力量构成分为冰火法师与雷冥法师。
当然除了常规的刷怪打BOSS的玩法外,作为一款主打PK玩法的网游,《决战轩辕》也准备了大量的PVP玩法。玩家仅需要集齐一套八档职业装备,就能在PVP和PVE玩法中获得爽快的战斗体验。游戏中的所有装备均可以通过打BOSS和刷野怪来获得,甚至是升级能所需要的技能书和各种宝石,都可以通过刷怪直接拥有。
无论是随时随地发起的门派宣战、自由PK,还是一周一次盛况空前的全服城战,甚至是刷BOSS时的冲突都有机会引发一场酣畅淋漓的全民PK。玩家积累的装备、等级亦或是技能优势都将通过PVP的舞台尽情展示。
《血杀英雄》
《血杀英雄》同样也是一款受《热血传奇》启发开发的专注于PK玩法的游戏,甚至某种意义上《血杀英雄》算是与《热血传奇》是师出同门。
《血杀英雄》的制作人陈浩健于2002年加盟盛大网络,曾参与《热血传奇》、《传奇世界》的运营和研发工作,并担任《热血传奇》的产品总监,可以说是国内最了解《热血传奇》的人之一了,《血杀英雄》则是陈浩健独自创业后推出的首款网游。
游戏采用全新的游戏引擎,打造精致的西式魔幻暗黑风格来奠定整个游戏的基调。在游戏中,玩家能看到魔法与刀剑相互碰撞擦出的绚丽火花,能感受到高操作模式战斗系统带来的超刺激PK快感。
《血杀英雄》不仅在画面效果上要求严格,还保持了传奇的“杀人爆装”等经典玩法,同时为了更加满足玩家日益变化的口味,游戏加入大量的PK向新玩法内容,丰富了游戏的战斗体验,让玩家既能感受到传奇的魂,又能感受到现代游戏的魅力。
《不败传说》
《不败传说》是一款围绕团队PK展开的MMORPG游戏,俗称国战网游。《不败传说》还原了传统国战经典的人海团战、载具攻城等大多数玩法,同时针对PK型与领袖型用户的乐趣需求进一步划分,削除经验系统,更加注重国战核心体验,以及个人荣耀感的培养,打造更加纯粹、人性化的国战机制。
为了专注于PK玩法,与市场主流的升级模式不同的是,《不败传说》甚至取消了经验系统,没有上班打卡式日常,没有海量日常任务、挂机打怪。每击败1个等级BOSS即可升1级。如果比主流玩家低了30级?别担心,你可以一口气打败30个等级BOSS,2个小时立即回归主流。
除了原有的大型国战活动,《不败传说》新增了“临时战场”“天空战场”“僵尸战场”3种即时PK战场模式,针对国战时间不自由、死亡回城跑图累、战场模式单一、PK规则单调等多点优化,让玩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自主规划时间,进入各大战场体验不同的人海PK乐趣。
《阿尔比恩OL》
《阿尔比恩OL》是一款中世纪欧洲魔幻风格的开放世界沙盒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其经济系统由玩家驱动,几乎所有物品均由玩家制造。游戏另辟蹊径,采用“人靠装备”系统代替职业系统,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游戏风格,自由搭配护具装备和武器。
游戏中的战斗系统不分职业,角色身上所穿的装备将决定玩家的游戏风格。战斗技能取决于身上穿戴的护甲和装备的武器,切换装备即可切换战斗玩法。玩家可以随时尝试新的装备,按具体情况更换武器、护具和坐骑。如想磨练角色的技巧,可以制造新物品,又或者直接换上自己最喜欢的装备。
在《阿尔比恩》这款游戏中,玩家在完成进入游戏后的第一个任务后,就进入了自由选择时间,此时的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任何游戏允许的事情,你可以杀怪削皮,砍伐树木的生活玩法,也可以去打怪刷副本等,不过如果要说其中最有特色的玩法无疑还是PVP玩法。
在《阿尔比恩》中的地图分为了黄、红、黑区域三张不同的区域,其中在红、黑区中可以随意进行pk,当然红、黑区域的资源也是最丰富的。游戏也保留了经典的爆装设定,在PK中一旦死亡那么角色身上的所有装备都会掉落,可以说相当的紧张刺激。
《大唐无双》
现在提起网易,估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氪金手游,不过在10年前,网易还拥有“自研狂魔”头衔的时候,也是曾经推出不过少经典端游的。由网易耗时四年研发,以“带给玩家真正的PK乐趣“为核心开发理念的“PK网游” 《大唐无双》就是一款让人印象深刻的游戏。
《大唐无双》以隋唐历史传说为背景,以隋末长安李氏新唐初兴、洛阳草莽聚义未散之际为故事起点,构建了“唐、义”两大阵营对抗下、任玩家尽情彰显豪情的开放式剧情世界。
创新的对立阵营无惩罚对抗体系;以及从野外遭遇战,定时阵营对抗活动,多种对等人数帮会战场、月度帮派联赛、到皇城争霸战等多层次海量PVP玩法;再加之独创的“以战养战”对抗回报系统,都会带给玩家最自由、刺激、高回报的PVP对抗体验。
当时的网易对于《大唐无双》的重视程度绝对是顶级的,除了铺天盖地的宣传之外,还专门邀请了当时刚刚拍完《叶问2》的甄子丹为游戏代言,甚至还专门拍摄了专门的电视广告。
虽然现在的网易专注于手游市场,不过《大唐无双》游戏倒是也依旧运营中,在2017年内还曾经推出过手游版本。
《星战前夜》
提起网游神作,对于广大玩家来说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暴雪的《魔兽世界》了,毕竟要名气有名气,要热度有热度。事实上,在浩荡的网游发展史上,有一款与《魔兽世界》同辈分、同样史诗传奇的游戏,据说真正的物理学家设计了它的数值和框架,专业的经济学家设计了它的商业和货币系统,而玩这款游戏的玩家,都是一群精英极客。这款游戏,就是《星战前夜》。
或许不少玩家初遇《EVE》都会被它的各种头衔、宇宙科幻背景所震撼,实际上本质上来说《EVE》的主打的游戏玩法同样也是玩家VS玩家的PK玩法。玩家在游戏中进行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与其它玩家战斗进行的准备。
在游戏的低安、0安区无时无刻不再进行数不尽的战斗,而死亡爆船损失所有的设定,也同样是经典的PK玩法设定,毕竟“一战爆负”才是最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设定。相信不少玩家也都看过《EVE》一场团战损失上百万人民币的新闻。
当然,上面提到的游戏仅仅只是诸多PK端游的区区一角,限于篇幅原因这里并不能介绍太多。各位玩家还玩过什么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PK网游呢?可以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
专访|席慕蓉:我给记忆命名,从此有了归属与顾盼
撰文 | 徐学勤
1949年秋天,出生于重庆的蒙古族姑娘席慕蓉,随家人为避战乱南下香港,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清苦而安稳的童年。五年后举家迁至中国台湾,她开始习画,并创作诗歌和散文,逐步成长为破销量纪录的现象级作家。八十年代,她的影响力开始溢出台湾岛内,作品被盗印、铺满了大陆的大小书店,与同龄的台湾作家三毛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众多文学青年的偶像。
1989年8月1日,台湾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赴大陆的禁令。8月底,她怀揣着无限的乡愁与热望,终于重新踏上了阔别四十年的大陆,回到祖辈栖居的蒙古原乡。到达大草原的那天晚上,当初识的亲人都已睡去,她在万籁俱寂的星空下忍不住号啕大哭。这一趟还乡之旅,成为她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此后的每一年她都会多次回到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到锡林郭勒,从乌兰巴托到克什克腾,翻越山川、草原、戈壁、大漠,去探访和记录游牧民族的生活,寻找潜藏于自身血脉里的历史文化基因。
1989年8月,在家乡的边界上,族人迎接回乡的席慕蓉。王行恭 摄
她的写作主题和风格亦随之变化,从以抒发个人爱情、乡愁与人生为主题,进行温柔、细腻、浪漫、多情的诗歌创作,转向以散文为主探索游牧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她写下了蒙古长调歌王哈札布、喀尔玛克流浪者丹僧、鄂温克女猎人玛丽亚·索等人的故事。近年来,她的写作向更早期的民族史延伸,创作出《英雄噶尔丹》《英雄博尔术》等一系列叙事长诗,以此纪念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的英雄人物。
与此同时,她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寻根也逐步深入。她的外祖父穆隆嘎
(汉名乐景涛,1884-1944)
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担任过民国政府监察委员、国府委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她的父亲席振铎
(蒙文名汉译为拉席敦多克)
毕业于辅仁大学,曾任民国政府参政员、立法委员,后长期任教于德国;母亲乐竹芳
(蒙文名汉译为巴音毕力格)
曾任国民大会蒙古察哈尔八旗群代表;二伯父尼玛鄂特索尔
(汉名尼冠洲,1894-1936)
曾任察哈尔盟明安旗总管,创办学社大力翻译出版蒙汉书籍,后因反对日本干预内蒙古自治运动而遭暗杀。
翻开那部厚重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她发现家人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内蒙古近代史上,他们曾为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抛洒热血,乃至牺牲生命。她的家族,牵连着蒙古境内的寻求族群存活的血泪史。对民族和家族历史渊源的追寻,让她明白自己与这片广袤土地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因而,自从她踏上那片高原,她在精神上就再也未曾远离。
她在文章中喟然长叹:“就是那里,曾经有过千匹良驹,曾经有过无数洁白乖驯的羊群,曾经有过许多生龙活虎般的骑士在草原上奔驰,曾经有过不熄的理想,曾经有过极痛的牺牲,曾经因此而在蒙古近代史上留下了名字的那个家族啊!就在那里,已成废墟。”穿越过幽暗斑驳的时空隧道,一切恍若隔世,她对故乡的情感愈发炽热奔腾。
她的散文书写也因此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当她彻底融入蒙古族同胞的大家庭中,成为其中名符其实的一员,她开始关注现代文明的一些更根本性命题,去追问何为现代,何为传统,何为民族国家。她为草原生态被肆意污染破坏而疾呼,她说草原不是只属于游牧族群,而是属于全人类,草原的生产力是依靠牧民、牲畜、草原三者和谐共处才形成的,一些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能需要千百年才能恢复原貌,而这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而今,年近八旬的席慕蓉依旧神采奕奕,才思敏捷,情感和精力饱满充沛,只是听力大不如前。她在年前推出了新的作品集《我给记忆命名》,这是一本日记与散文合集,书写时间横跨半个世纪,涉及诗歌创作、还乡之旅、家族历史。她说,有些事物如果再不记下来,恐怕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因此,“我给记忆命名,或许,它们就会有了归属,有了顾盼,有了呼应。我给记忆命名,只因我的痴心。”
无论身在何处,她始终笔耕不辍,她说现在才是自己创作的真正“高峰期”。她仍旧在努力书写新的英雄叙事长诗,还受到叶嘉莹、齐邦媛、痖弦等前辈的指点和鼓励。对她的采访,正是在她赴天津参加叶嘉莹的学术研讨活动之后,她们相识近二十载,有着同族情谊,更有着诗人灵性的契合相通,我们的谈话也由此开启。
与叶嘉莹的两次还乡之旅
新京报:最近,你到南开大学参加“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你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也多次谈及叶先生对你诗作的评点。你们都是蒙古人,因诗歌而结缘,你还曾陪同她一起去叶赫河寻找原乡,能否谈谈你们相识的经历?
席慕蓉:多年来,我一直是叶先生的读者,可是我对古典诗词仅仅是喜欢,很多东西也不见得能真正领会。我们的相识,缘于我的好友、台湾成功大学戏剧教授汪其楣的一番好意。她是叶先生的学生,2002年3月,叶先生到台湾讲学,她给叶先生寄了一篇刚发表的论文,里面谈到我的一些以蒙古为主题的散文和诗,她还让我也寄一本刚出版的散文集《金色的马鞍》给叶先生看。过了几天,叶先生说想要见我,她让另一位学生施淑教授来邀我共进晚餐,这让我喜出望外。
叶先生见到我就说,“我也是蒙古人,我们的部族是叶赫那拉。我的伯父曾经告诉过我,叶赫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它的地点,也不知道如今这条河流是否还在。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它。”那条河流仿佛是她记忆的根源,我说,“那我们就去找一找吧!”她说,“好的,如果你找到了叶赫水,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听到这个“命令”,我心里很惶恐,我怎么可能找得到?不过幸好有一位朋友,在沈阳住的内蒙古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他帮忙委托满族朋友、《沈阳日报》的记者关捷先生去找,过了三个月,好消息就来了——叶赫水至今犹在,它在吉林省梨树县,是一条很美的河流。
我赶紧向叶先生报告。当年9月,我们终于成行了,还请来吉林大学的朋友做向导,一群人陪着叶先生回到她念念不忘的原乡。虽然叶赫水还在,但是叶赫那拉部族从前的居住地已经没有了。有人带我们去看为拍摄电影而盖出来的宫殿式建筑,那是假的,叶先生说想要去看真正的城楼旧址。他们就带着我们来到一片玉米田,以前我只知道草原可以延伸到天边,我不知道原来玉米田也可以伸到天边。那天傍晚,红红的太阳被尘霾遮住,秋天玉米的叶子有点干枯,风吹过来的时候发出沙沙声响。
玉米田的远处有座稍高的土台,一位同伴怕叶先生走冤枉路,就先跑到土台上面,然后回头对叶先生说,“您不要上来了,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虽然是善意的劝告,但幸好她没有听从。那时候她已经78岁,但身体很好,大家都想要搀着她上去。我那时有了一点点经验,就是我回到内蒙古老家,很多朋友都好意地陪着我,给我介绍,但等到回去后我才后悔没有好好看一眼,其实有时候需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所以,我就跟那些朋友说,我们不上去了,让叶先生一个人到土台上看看吧。
叶先生慢慢走上土台,眼前是红的、紫的、褐的、墨绿的玉米和荒草,微风吹拂着,她在台上独自伫立了好一会儿,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不就是那首黍离之悲的诗吗?我现在的心情,怎么和诗里说的完全一样?‘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因为是在故土之上,所以土地跟她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应,当她站在一座别人眼里“什么都没有”的土台上,她却遇见了那首三千年前喟叹黍离之悲的诗。
2002年,叶嘉莹(左)与席慕蓉在叶赫河畔。
新京报:后来叶先生81岁的时候,你又陪同她去了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这听起来是很大胆的举动。
席慕蓉:是的,听起来有点危险,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说要给我颁“最佳勇气奖”,我说应该给叶先生颁奖。2005年,叶先生对我说:“其实还可以去一下蒙古高原。”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巴尔虎草原,还登上了北魏拓跋鲜卑先祖所居石室嘎仙洞。她成为百年来家族里第一个回到蒙古原乡的人,一路上她神采奕奕,诗兴大发,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口占绝句一首,记得其中一首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我也问过叶先生为什么早不回来,她说怎么可能?又是军阀混战,又是抗日战争,又是国共战争,又是漂泊海外,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我非常高兴能有机缘陪她回家乡。其实,一路上我们有很好的越野车,也有朋友帮忙安排行程,路上并不危险。她当时身体也很好,没有出一点状况,反倒是我自己感冒了。
对绘画有强烈企图心,而写诗是生命本能
新京报:你在书里引用叶先生的话说,“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似乎人人都可为之。但也有人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门类中最依赖天赋和灵感的,是难以训练出来的。在你看来,叶先生的古典诗词教育对写诗有多大的帮助?
席慕蓉:听过叶先生的演讲,我才知道什么叫“诗教”。我不是学文学的,没有受过专门的古诗训练,比如平仄、音韵之类,我只是在大学时期跟溥心畲老师学过一点,但是也完全不会用,就自己乱作。我曾听一位学者说,“字是不会说谎的,人会说谎。所以,人在修改的时候,就把不说谎的字改成了说谎的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这个观点说给叶先生听,原来那位学者也是她的学生。她说,“你以为是你选择了这个字,其实是字选择了你,字比你想到的还要早。”
叶先生是世间罕有的教师,她讲课跟一般的中学、大学老师完全不同。比如讲辛弃疾,听她讲完以后,再读辛弃疾的作品,会有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不是说其他老师讲得不好或者不对,他们都是启发过我们的人,能碰到一位好的语文老师,就是遇到人生的贵人,因为他们能把学生心中某些灵性的东西挖掘出来,可是他们跟叶先生是没得比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听叶先生讲课,她讲到一句话,结果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很多人都看到我,但我就是无法控制。她当时是解析欧阳修的《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讲到“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一句,欧阳修写采莲女子低头看水面,人脸和花互相映照,心里产生像丝一样乱的感觉。女孩察觉到自己的美丽,当其他同行的伙伴都已走远,她却流连忘返。
叶先生说,这是欧阳修的神来之笔,欧阳修的深意是从表面的美丽牵连到一个人内心的向往和追寻,那才是生命暗藏的美好本质。她说,“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机会知道和认识自己的美好。”哇,真是吓死人!这句话仿佛贯穿天地万物,她所悲悯的不只是那个“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的采莲女子,而是尘世间所有的生灵。突然间,我的心怀像是完全被打开了,仿佛多年的彷徨和委屈全部都消融在这句话里。
1993年,席慕蓉油画《月光下的白马》。
新京报:你曾在诗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的序言中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一无所求,“从来不必以写作作为自己的事业,所以可以离企图心很远。”这与你在画画上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何对写作没有企图心?企图心对艺术创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人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企图心?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画得好的时候,你会嫉妒。我以前只要看到人家画得很好,就想什么都不干了,立马回家去画画;有时候也很坏,看到别人画得不好,就有点暗自得意,当然这对一个所谓艺术家来讲,是很糟糕的东西。但我后来读到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说创作者的嫉妒心是一定会有的,但嫉妒不是要去害别人,把别人的画刮破,而是去思考他怎么比我好,我为什么不能做到那样,这种情绪其实是健康的——我嫉妒了,但是我不要去陷害他,而只是“陷害”我自己——回家去画画吧,别旅行了。虽然有时候回去也不见得会怎样,但那种对自己的责备,其实就表明有企图心。
但我对诗歌绝对没有这种企图心,当我读到一首好诗,会恨不得跟所有朋友分享。比如,我刚拿到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翻译的蒙古国诗选,还跟他要了几本送给朋友,因为诗选都是从早期诗人讲起,我害怕朋友们看到开头几页觉得没兴趣就停了,所以跟他们说,你们先看其中当·尼玛苏荣的那首《四季》,我觉得那首诗美到不行,全诗分四个段落,共有225行。可以试读几段:
故乡从很远很远就映入眼帘很美
噙满泪水的眼睛里溢出热泪最美
站在马镫上吹着口哨飞奔很美
飞奔的马蹄之间鸟儿穿梭更美
……
有谁过来唱歌很美
有谁离去悲伤也美
放不下的爱在心中化作旋律很美
流转不停的时间不忘敲钟很美
……
后来,一位诗人朋友说他们有一个语音平台,问我要不要去朗诵这首诗。我说我要,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在做过之后,好像都会遇到一些更好的机会。
前天晚上,内蒙古诗人宝音贺希格来陪我过中秋,他翻译过我的诗,也是一位好得不得了的诗人。我跟他说,我喜欢这首《四季》,他说整个蒙古高原没有人不喜欢这一首。然后,他打开手机给我听一位专业朗诵者的朗读,就发现“……是美的”用汉文来表现过于平白。我跟他说,我要借用那位朗诵者的蒙文原文朗诵,但前面先用汉文读一遍,不然别人听不懂。你看,我是多么乐于跟别人分享好诗,我发现人家写得比我好,那才是最大的快乐。
所以,我对画画和写诗的差别就在于此。读到一首好诗,我就会“人来疯”,可是我自己写的诗,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解,也不想讲。我觉得写诗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喜欢就写。如果让我去讲怎么写诗,我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叶先生的了不起,就在于她把所有古典诗词里的人,以及诗词中的深意和神来之笔讲给我们听。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清楚。当然,她是用自己的一生做到的。
新京报:在你的书里,似乎很少看到“文学”这个字眼,你一般会直接说诗或散文,文学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文学”说得那么少吗?我倒不觉得。对我来讲,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去阅读和吸收,二是去写作。阅读让我发现文字的美,寻找到与自己相近的灵魂。有的作品,初读和重读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重读可以获得很多之前读不到的东西,可是非得经过幼稚的初读,才能重读到那些东西。我想文学就是这样,要用一生不断地初读和重读,你问我要如何解释文学,我可能不太会形容。
我现在的理解力绝对比年轻的时候好,这是年龄增长的好处。那天,一个女孩儿问我,会不会为年老而悲伤?我说,“我的每个关节都觉得悲伤,可是我的理解力觉得愉悦。”所以,文学是让我心向往之的事情,当一不小心遇到一首好诗,我就会打电话告诉朋友,对我而言,讨论文学是件很快乐的事。当然,如果说要规规矩矩坐下来读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诗集,有时候也会很累,最好的遇见是一不小心突然间撞到,那种感觉是最美妙的。
席慕蓉画的荷花。
新京报:你说对写作没有企图心,但其实你的写作比画画影响力更大。
席慕蓉:画画是我的功课,我在绘画方面有强烈的虚荣心,希望能画得好。至于有没有天赋,到现在为止,我想还是不要知道答案吧。在写作方面,我不需要知道答案,因为我的写作其实是在整理自己,有的时候想不通,我就会写日记,有的日记写得还很长。譬如跟叶先生见面,我可能当时来不及写,但事后肯定得补上,有人说这些文字就像散文,不像日记,可是我就是这样写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不要忘记,我不会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有年轻朋友问,要怎么写一首好诗?我心想哪有那回事,开始去写就好了。我很年轻时就开始写诗,比画画还早,喜欢的可能就拿去发表,不喜欢的就塞到抽屉里,有时候隔几年再拿出来看,觉得“唉,还不错”,连改都不用改。有一次我投稿到《联合报》副刊,那首诗是有点想要写,却又觉得不怎么样。但那天在报上看到诗人许悔之写林文月先生的一首诗,我的天哪,他写得那么好。我赶紧打电话给《联合报》的编辑,说你看今天许悔之写成这样子,拜托你把我的那首诗撕掉吧,不用寄回来给我了。
我的写作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我非写不可的,我会用散文把它们写出来。比如《丹僧叔叔》,写一位喀尔玛克蒙古人流浪的一生,那样的文章是我努力写出来的。
1991年,席慕蓉与八十岁的父亲在台北。
诗,是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
新京报:你说《古诗十九首》和古乐府给了你最初的诗歌启发,你的诗歌中有很多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化用,同时你也很推崇纪伯伦等西方诗人的作品,你的诗歌创作受哪些人的影响比较大?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你是如何融合接续的?
席慕蓉:我不知道,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但是我记得在香港读小学时学古诗词的经历。那时正逢乱世,老师们其实都不是标准的小学老师,不像现在这样规规矩矩地从笔顺、拼音开始教,所以,我的孩子们都说我写字笔顺不对。那时候老师也跟难民一样,生活很苦,他们的学历可能很高,可是还得教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就让我们多背诵。我到现在还能背诵很多诗词,能把《琵琶行》从头背到尾,小时候背的这些东西就烙印在脑海里。读《古诗十九首》也是因为喜欢,我当时就感慨,天哪,这些诗每个字我都认得,尤其前面几首都那么简单,但当它们组合到一起怎么可以这么美?
你现在要问我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是骄傲得不回答,而是真的没办法回答。我以前跟人家说,我没有受过任何诗歌和文学的教育,可是后来想,我好好地上过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国文课,算不算受过文学教育?到国外以后,我读到一些法文诗,像纪伯伦等人的,我感觉到音韵之美和翻译之难,这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感受,没有系统性。
以前人家问我受谁的影响,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可能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在绘画方面也是如此,我不会标榜自己属于哪个画派,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写生者。我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说我喜欢谁,但对他作品的来龙去脉和艺术特色不见得能说清楚。但我读他的诗,就知道他的东西了不起,比如商禽、痖弦、陈义芝,我觉得他们的诗里有些东西是我永远进不去的,或者,我能进去但永远不会那么写,但是我很高兴有人那么写,而且写得那么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青年席慕蓉。
新京报:你的诗歌创作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
席慕蓉:我觉得是现在,是此刻!我当然珍惜年轻的时候写下的诗篇,不过,我到现在才明白,过往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此刻,此刻正是一个创作上全新的起点。所谓“高峰”不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是我自身察觉的热度。是的,是一种追求的热度,如今的我,真是全心全意在追求我想要写的英雄叙事诗。从2010年夏天写出第一首《英雄噶尔丹》开始,到现在还没停止,非常奇妙!我自己曾经写过的句子竟然成真:“我相信,诗,只能从自己出发,并且是一个不可动摇、不被利用的自己。”到这个年龄还能拥有“不可动摇、不被利用”的热情,我知道,这是故乡大地给我的力量,我深深感激。
年轻的时候写诗和现在的状态是不同的,我最近发表的一首《绝句》很能说明这种变化,“昨日是以诗来寻觅,那躲藏着的自己;如今却以自己来寻觅,那躲藏着的诗。”
新京报:1949年之后,在台海相隔的情况下,台湾出现了纪弦、余光中、洛夫、痖弦、商禽、郑愁予等一大批诗人,你与这些前辈诗人的交往多不多?
席慕蓉: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很多,有的有过一些交往。我读的第一本现代诗集是余光中先生的《蓝色的羽毛》,那时候我在读中学,有一次堂哥带我去逛植物园,出来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买本书,我就在路边买了这本诗集。因为我之前也在文章里写过此事,很多人就说那是我的诗歌启蒙,但我觉得不是。我很敬佩余先生,我们也常常合作朗诵诗歌,他对我也很好,但其实我在买这本诗集之前就已经写了两三年,我只是余先生的一个读者而已。
记得有一次,余先生来看我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画展,是用激光做的版画,他那天来了三次,他很喜欢一幅《孤星》,就对我说“这一张给我做封面吧”,后来那幅画就成为他的诗集《与永恒拔河》的封面。我很尊敬余先生,他的学问那么好,对晚辈也很友善,但是真正开启我的写诗之路的其实是痖弦。痖弦一直担任《联合报》副刊的主编,我投稿到《联合报》,他常刊登我的诗,还带着同事来我家看我作画,对我很鼓励。
那时候我还年轻,一下子给他寄了三十多首诗,我对他说,我不是要投稿,只是想请他帮忙看哪首好,哪首不好。他就真的用铅笔帮我在每首诗上画勾,再寄回给我,有的画一个勾,有的画两个或三个,有的不画,我就明白了那是他的评价。他曾说过一句话让我很受用,因为那时候我的诗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很多刊物都向我约稿,还让我附上插画,有一次开会,他特地走过来对我说,“你不要沦落成一个‘写稿妹’,有些要求你要懂得拒绝,好好地写自己的,不要谁让你写你都写。”这句话我听进去了,真的十分感激。
所以说,痖弦是我在诗歌道路上的引路人。我原来不会回答“受谁影响”这个问题,现在知道要怎么回答了,要谢谢你。我是从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开始注意读现代诗,然后是痖弦把我带上路,直到现在,我还会把正在写的英雄叙事长诗寄给他,请他帮忙提意见。我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里也写到,齐邦媛和叶嘉莹先生都“责备”我,而痖弦先生不好意思“责备”我,只是说我的叙事诗里应该有一些“埋伏”,所谓“埋伏”就是突袭,突袭进人的心里,让读者不会忘记这些句子所带来的惊喜交集的美好感觉。我原本是一个外行,进入所谓的文学界,我是蛮有自卑感的,我不是学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只是个闯入者,幸好有好的老师和朋友。
《我给记忆命名》席慕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
新京报:你早期的诗作大多围绕爱情和人生主题展开,注重个人情感的挖掘和抒发,你与丈夫刘海北先生的爱情很幸福美满,为何会写出那么多忧愁伤感的诗句?你的诗歌一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席慕蓉:我写诗需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年轻时我有两个孩子要管,幸运的是有人帮我做家务,我主要管孩子的洗澡和睡觉,等孩子的事都料理妥当后,我就开始写诗。我的很多伤感的诗,都源自年少时所受的伤。由于战乱,我的少年在漂泊动荡中度过,跟随家人颠沛流离,白天像一只小野兽在森林里想办法逃跑,晚上再回到洞穴里慢慢流泪。因为找不到朋友,日记本就成为唯一的朋友。
有人说,席慕蓉设想了很多情境来写诗,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人在少年时期特别敏感,自己受伤或者让别人受伤,很多诗也都是在寂寞受伤时写的。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诗是一个困惑的人用一颗困惑的心,在辨识着自己此刻的处境。我在诗中的感情,绝对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拟设。所以我曾经写过,“诗是挽留,为那些没能挽留住的一切;诗是表达,为当时无法也无能表达的混乱与热烈,还有初初萌发的不舍;诗,是已经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如果,如果曾经是可能……”
新京报:你以前说写诗是从不强求的,但近几年写蒙古英雄叙事长诗,却“一再要求自己去写,仿佛是日夜都放在心头的愿望”,为什么会有这种愿望?叶嘉莹先生说你的叙事长诗不如抒情诗,这些诗歌成就可能不高,齐邦媛先生也说你“不够强悍,写不了史诗”,你对她们的评价和建议作何感想?
席慕蓉:之所以要写英雄长诗,是因为回到内蒙古老家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无比丰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外界所不明白、也不想去了解的,但对我而言是一个诱惑,我想慢慢地把它们写清楚,算是给自己的一份奖品。别人说我是有使命感,是在捍卫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不是,我就是遗憾前半生没有办法仔细了解自己的原乡,遗憾自己民族的英雄处在一个被误解的状态。在草原上,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着的英雄人物,在汉文史书上记载的却是极为表面的功过,甚至误解,我也不能说这些记载是错误的,可是总觉得那些解释距离游牧民族的时空真相太远。
我向叶先生坦承,我知道自己写得不好,达不到渴望中的那个标准,可是这些年在心里翻腾着的都是这些英雄的事迹。她说,如果是生命自身散发的愿望,那就去写吧,唯有听命而行,才可能实现生命自身的要求。因此就算诗的成就不高,也是值得去完成的。听到她的意见,我仿佛一切都变得明朗了,没有负担了。我非常感激叶先生和齐先生,现在我依然努力在写,一天到晚都在改。
从个人乡愁转向对游牧族群的关注
新京报:你的书写从个人乡愁转向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和代表人物的关注,写下了歌王哈札布、丹僧叔叔这样的人物故事,这种转向是如何发生的?
席慕蓉: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要感谢两位先生,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的贺希格陶克陶教授,他曾为我的《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写过序言,把我对蒙古题材的写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的乡愁,第二阶段是对族群文化的认识,第三阶段是更开阔的对大自然的认识。另一位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张弛教授,2016年在台湾东吴大学举行的“席慕蓉研讨会”,他发表过论文,研究我的写作主题和风格的转变,我很惊讶他是怎么看出来的。2019年,台湾出版了关于我的研究文集,选了他们俩的文章。
我前半生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原乡,1989年当我46岁第一次回去时,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没想到此后的30年我还一直在跑。近些年,在我母亲的家乡克什克腾的草原上,我追踪几位牧马人的生活,除了录音访问外,还与一位当地的摄影家合作,追拍马群的家庭生活,从小马驹出生之后开始记录。
2019年9月,席慕蓉参加“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京报:你对游牧民族持续关注数十年,除了血缘因素,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对你有何特殊吸引力?
席慕蓉:你进去之后就知道,我们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所谓环保运动,而游牧民族要早几千年,游牧民族对大自然最为疼惜,知道如何跟自然和谐相处,里面的学问深得不得了。不要小看牧民,如果研究牧民跟大自然相处的种种细节,是可以写出博士论文来的。几千年来,游牧民族在那样脆弱的生态环境里生活下来,要知道草原不是天生就那么好的,草原的生产力是靠牧民、牲口和草原的和谐共处才得以维系和发展,而这些东西是包括我在内的受汉文化教育的人不太了解的。不只是东方如此,西方人对欧洲北部游牧民族文化的了解也很有限,把他们放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如果我们把将生态维护得这么好的族群视为落伍,认为它在现代文明到来的时候应该消失,那么,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何为现代文明?在很多人眼里,它似乎等同于所谓科技文明,好像只有拥有科技文明才有资格活着,难道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不是现代活着的人吗?我们对“现代文明”的定义不应该太狭隘,如果敢用“现代文明”这四个字,就得对现代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负责任。我很喜欢比尔·盖茨推行的“大历史”概念,如果把宇宙的全部历史浓缩成一天,那么人类不过是半夜才出来的。从某些角度而言,人类实在是可恶的生灵。以现代文明自居的人类,如果只是把计算机、移动通讯、远程教育传给游牧民族,那对游牧文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如果到草原上大肆发展工业、农业,毁掉草原的生机,那就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新京报:你在《独幕剧》一诗中说,“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让我们静静憩息/当作是心灵的故乡/这也是我们最深的困惑/整整一生都要在自己的/家园里扮演着永远的异乡人”。你们这一代在台湾被视作“外省人”,回到内蒙古虽然有大家庭的温暖和归属感,但同时也有着异乡人的孤独,你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情感?
席慕蓉:这首诗应该是刚回去的时候写的,那时候绝对是诗里所说的这种情绪,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刚开始,对原乡的情感完全控制了我,可是现在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现代人类。昨天,一个朋友说蒙古人有很多悲悯之心。我说不对,不只是蒙古人有悲悯之心,是全部人类都有悲悯之心。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国家和民族的疆界没有了,不是要做世界公民,我认为仍然需要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这样世界才会有吸引力。如果我把蒙古的英雄叙事长诗写出来,我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蒙古人,因为我变成了完整的蒙古人,我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的理解力让我变得对自己更宽容了。
席慕蓉(2013年,王纪言摄于香港书展)
新京报:你们这代台湾人都有乡愁,现在的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情感是怎样的?
席慕蓉:我不能替别人回答,因为没有观察,我只能说说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尤其是女儿)觉得我挺麻烦的,因为经常读一首诗或听一首歌就流泪。在他们小时候,有一次带着他们去买童书,我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那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当时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两个孩子回过头问怎么回事,说“这是童书,你在哭什么?”我就给他们看这首词,我的女儿说“你就是麻烦!”,然后把书放回书架里,而我的儿子比较贴心,他把那本书拿出来,说“妈妈,我们今天就买这本吧!”
后来我女儿到美国学音乐,她是弹钢琴的,现在在美国的大学里教钢琴演奏。1995年,她刚去的时候,有一次突然半夜打电话给我说,“妈妈,我以前老是看见你听着唱片流泪,觉得你很麻烦,很无聊,可是我今天知道你为什么流泪了,因为今晚蒙古族的图瓦合唱团来我们学校演唱,他们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开始掉眼泪,真是好奇怪。西方的同学也说他们唱得真好,可是只有我知道歌里的孤独与寂寞,好像跟我靠得很近,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哭了。”然后她说,“妈妈,你带我去蒙古吧!”
我的儿子更是,儿子崇拜他的外祖父,外祖父健在的时候,他就去过蒙古国;后来外祖父走了,他特别想念,也跟着我回到内蒙古。所以,你觉得需要担心吗?从我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时间到了,他们对原乡的感情自然就会迸发出来。
新京报:读到你写的蒙古歌王哈札布的传奇故事,我特地找来他的音乐听,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同样让我有流泪的冲动。
席慕蓉:哇,他的长调真是不得了,你会觉得那是从天上来的声音,长调一定要用蒙语唱,不能翻译,因为歌都是从母语里生长出来的。蒙古长调之所以被举世推崇,不单在于它的美丽和艰难,还在于它能把歌者和听者都提升到一个美好的高度,这个高度是在一般的生活里难以达到的,但又是从远古以来,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渴望企及的。能够听哈札布觉得感动,我们就是有共鸣的。
撰文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走走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