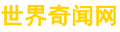把孤独当做晚餐什么歌(网易云热评: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聊天记录。)
把孤独当做晚餐什么歌文章列表:
- 1、网易云热评: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聊天记录。
- 2、年过四旬仍未婚的8位女星,个个美若天仙,你最想娶谁?
- 3、哈佛医师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
- 4、希望我的绘本简洁又有力,像石头或贝壳
- 5、别把孤独当晚餐,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致当代年轻人
网易云热评: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聊天记录。
网易云热评:“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聊天记录。”
今日建议,忙起来就没时间难过了,让自己廉价的事不要接受,有些人的相遇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别纠结了。
一一网易云热评《把孤独当做晚餐》
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黯淡了,成为宇宙里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网易云热评《年轮》
给你系鞋带的人 。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 。你哭时在一边看着你的人 。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时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老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 。是你应该去珍惜的人。
——网易云音乐《错过》
不要跟别人交心吐露太多,因为你迟早会发现自己会后悔的,讲真,交心这件事,很幼稚,我倒不是鼓励你变得复杂,我只是希望你能学会保护自己。
—— 网易云热评 《胆小鬼》
宫崎骏《幽灵公主》里的一句话送给受伤的你:“不管你曾经被伤害得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
——网易云热评《放过》
20多岁的你迷茫又着急,你想要房子你想要汽车,你想要旅行你想要高品质生活,你那么年轻却窥觑整个世界,你那么浮躁却想要看透生活,你不断催促自己赶快成长却沉不下心来认真读一篇文章,你一次次吹响前进的号角,却总是倒在离出发不远的地方,晚安熬夜的人们。
——网易云热评《这个年纪》
谢谢小可爱们的关注(此文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年过四旬仍未婚的8位女星,个个美若天仙,你最想娶谁?
加缪曾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当今社会,大多数年轻人都抱有宁缺毋滥的心态,把孤独当成晚餐。在娱乐圈中,也有这样一群女明星,年过四旬却仍然是单身贵族。
许晴气质优雅,她的感情生活也是一波三折。许晴曾有过三段感情经历,但都无疾而终,其中与王志文被誉为金童玉女。
命是弱者的借口,运是强者的谦辞。许晴放荡不羁的性格,让她在时隔多年后依然我行我素,不惧世俗的眼光。
人生十分孤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另一个人,每个人都很孤独。在一次采访中,秦岚引用了黑塞的这段话。
白月光姐姐秦岚的情史略显单薄,她和陆川、黄晓明都有过恋爱经历,但令人惋惜的是与黄晓明的感情,因angelbaby的插足不了了之。
娱乐圈的大才女徐静蕾,可以说配得上她的人凤毛麟角。她曾告诫观众:有的人认为坚持会让我们更强大,其实有时候放手也是。
插足王朔婚姻,与高圆圆争男友,徐静蕾的情史风流潇洒。无论是做演员、当导演,还是写博客、练书法,她都做到了极致。
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家境优渥,欲与天公试比高,徐静蕾的人生观豁达开朗,这也是她至今未婚的重要原因。
她是落选港姐,却也是全港情人,被誉为最美周芷若的她,金庸都直言想把张无忌许给她,她就是周海媚,一个有过九段情史的奇女子,如今却仍旧形单影只。
周海媚曾告诉朋友:想结婚就去结婚,想单身就维持单身,反正到最后你们都会后悔。
又美又飒的陈法蓉,曾是香港的新生代女神,但是自己的两段感情都遭到周慧敏横刀夺爱,也是令人唏嘘不已。
陈法蓉曾在港姐总决赛上豪言:我参加比赛就是为了赢得冠军。可就是这么一位霸气的女星,却在感情生活上屡战屡败。
当年因为《寻秦记》而喜欢上古天乐和宣萱,两人这几年也是经常传出绯闻,但大多都是空穴来风。
宣萱的学历很高,个人也极具涵养,在经历了5次无疾而终的感情后,她也是选择了躺平,毕竟自己现在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也算是待价而沽。
宣萱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她不会为了结婚而去结婚,在她看来:生活可能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最终受伤的地方将会是最强壮的地方。
女强人李冰冰事业心太强,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聊感情话题。但是从学生时代起,李冰冰就不缺乏追求者,任泉更是等了她十几年。
受到良好教育的李冰冰,从小便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在她的感情生活中,她也是不卑不亢。在经历了多次的感情挫折后,她也是直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李冰冰曾说:年龄一大,相信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既非玩世不恭,也非生性多疑。只是在历尽千帆后,一切都显得云淡风轻。
我在自己周围筑起围墙,没有人能进来,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俞飞鸿是经历了何种非人的遭遇,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
有人说俞飞鸿是为了等窦文涛才一直未婚,甚至连清高自许的许知远都表示:一想起你,我这张丑脸便泛起波澜。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枝头,绿了芭蕉。然而,在俞飞鸿身上时光似乎驻足了,年龄越大反而越有魅力,很多网友甚至直言: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人间盛世颜。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是它一直在那里。离别和孤独是人生的常态,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才能保持真我,诗意生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屏幕前的你婚否?
哈佛医师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
原作者|[美]凯博文
摘编|沈书枝
凯博文是国际医学人类学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四十年。2009年,他的妻子琼·克莱曼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也即俗称的“老年痴呆”。凯博文随即投入对妻子日渐艰辛的照护中去,经历了妻子的病情由初期发展至严重,最后在十年后去世的过程。
目前医学界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因和病理学还所知甚少,迄今为止也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患者来说,家庭和社会照护网络实际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患病的是病人的大脑,家属需要一起面对的,却是漫长的现实生活。照护漫长、疲惫、灰暗,常常使人感觉绝望,但也有着因为共同的努力而产生的平静闪光的时刻。它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同时却又充满意义,使得照护者与所爱之人的生命联结得更加紧密。奇怪的是,尽管这是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来自医疗系统的支持却是少之又少。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内容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拟。
《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美]凯博文 著,姚灏 译,潘天舒 审校,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版
一、作为主要照护者的最后几年,
是黑暗的时刻
每当我想起琼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她患病的终末期,而是我作为她的主要照护者的最后那几年——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主要是四个字——“黑暗时刻”。在情况最坏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是在“忍人所不能忍”。我曾经与许多家庭照护者交谈过,他们在亲人得了痴呆症,特别是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我那种感觉。艰难总是开始于某些不起眼的事情——也许只是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得到任何回报。接着,挑战会逐步升级为绝望与彻底的疲惫。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无望与无力的感觉又会扑面而来。每种疾痛体验都会有独属于它自己的、令人心碎的细节,但都面临着某种必然,那就是:随着痴呆症的发展,照护中的糟糕时刻会迅速累积,并最终达到某种程度。到那时,家庭照护者要是不曾接受过任何有关照护的训练,就会轻易被打垮。
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那十个年头里,琼好多时候都会出现短暂性的激越状态[1]。而到了最后几年,那种激越状态会长期维持在某种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却不再消失了。平静与安宁的日子已经离我们远去。此外,琼的这种显著的焦虑情绪,就像背景噪声似的,有时甚至会演变成狂乱。而且这种不受控制的过度活跃状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持续几分钟,而是会持续数个小时,有时甚至超过一天。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任何口头上的抚慰都无济于事。镇静剂的作用也很小,已经无法控制琼的症状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然后,琼会瘫倒在地板上,那时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这种分外可怕的状态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违拗症状[2] (或者可能此前就已经存在了),其首发表现就是对抗。她不再像往常那样配合我们的照护工作,而是会抗拒任何人的帮助,有时甚至还会抗拒下床、抗拒冲澡、抗拒穿衣服。对于周围的人,她还会发表负面评论,这是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表现。比如,她在麦克莱恩医院老年神经精神科住院的时候,无法忍受她的几位病友,尤其是某几位吵吵闹闹、自以为是的病友。于是,琼对着他们吼道:你们这帮“粗鲁的”“叫人作呕”的家伙。后来,琼的这种违拗症状甚至开始针对护士、护工和医生。她会批评他们,拒绝他们的帮助,还反复辱骂他们。这与以前的琼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当我看到她这些行为的时候,内心惊讶万分。不管是谢拉、我,还是我们的家人,都无法控制琼的这种激越表现,也无法控制她的负面情绪以及攻击行为。
琼变得很容易大发脾气,时不时地就会与现实完全脱节。我们没有办法和她讲道理,也没有办法使她冷静下来。最糟糕的时候,她会陷入谵妄,拳打脚踢,大喊大叫,对任何人所做的或者所说的都毫无反应。和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的照护者一样,这是照顾痴呆症患者最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之一。
凯博文与妻子琼·克莱曼,摄影:托本·埃斯克洛德
关于那些日子的回忆,此时正在我脑海中翻滚,它们凝固成了一系列充满冲突的痛苦时刻,久久不愿散去。有一次,我们去波士顿金融区见一位律师。这次会谈,气氛紧张,非常费神。熬到结束,我们乘坐办公大楼拥挤不堪的电梯准备下楼。在会谈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些在痴呆症病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法律问题,比如家属的代理权与监护权问题,又比如是不是需要去找一位医疗代理人,还有我们的遗嘱问题。讨论的过程非常艰难,也让琼感到非常困惑,非常焦虑。当时,我们乘坐着电梯,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一帮年轻姑娘急不可耐地冲出去买午餐。琼一下子被挤远了,几乎摔倒在地。可那帮姑娘,谁也没有停下来,看看她是否安好,也没有谁向她道歉。琼被吓坏了,她呆坐原地,不肯起身,这就叫我很为难,因为我没法儿把她挪到安全的地方去。我感到怒不可遏,倒不是因为琼,而是因为那帮冷漠无情的年轻员工。一个残疾人被她们撞倒在地,可她们却当啥也没看到。
还有一次,为了庆祝琼的生日,我们去波士顿的一家高档餐厅用餐,同去的还有我的母亲、弟弟和弟媳。能去外面吃晚饭,这感觉很好。但当我们落座时,琼却猛地跳了起来,开始对我大喊大叫,显得非常生气。她说她已经不是小孩儿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不需要我帮她坐到椅子上去。几分钟以后,她又从椅子上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喊叫,因为她发现我们没给她点红酒。可实际上,这是医生的要求,她在用药,这期间是不能饮酒的。只是这次不像第一次,她的喊叫没有停止。即便我后来退了一步,给她要了一杯鸡尾酒,她依旧没有停止吼叫,终于引起了骚乱,吵到了店里的每一个人。在那之前,我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因此我知道这种事情到了最后总会升级。琼可能会陷入疯狂,进而完全失控。当时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立即带她回家,因为感觉餐厅里的压力对她来说可能太大了。但最后我还是让她留了下来,因为我真的好想让她参加这样的家庭聚会啊。
这顿晚餐,进行得并不顺利。它本该是庆生晚宴,结果却更像是一场灾难的序幕,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每隔几分钟,琼就会发一次脾气。在吃完甜点后,我们准备起身离开。我给琼套上外套,然后牵着她离开餐厅,却遭到了她的竭力反抗。当我们走到门口时,她依旧在使劲叱责我。我们准备去开车,她却不愿牵住我的手。于是,我只好也冲进熙熙攘攘的车流,以防她被过往的车辆撞到。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扬言要跳出车门,结束这一切。等我们终于回到家,她已经变得相当狂躁,相当激动了。她撞翻了一张小桌子,把墙上的装裱画和其他东西统统扔到地板上。她已经完全失控了,我担心她会伤害到自己。同时,我也几乎无法再克制自己心中的愤怒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忍耐下去,而且我这么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不肯换衣服,也不肯上床睡觉,最后径直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我拿来一条毛毯,盖在她身上,然后呆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但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又一切如常了。对于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她居然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们会睡在客厅里?”她这么问我。
另一次发作,是在纽约。光是能去到那里,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是小小的胜利了。坐飞机,我可不想冒这个险,还是决定自己开车过去。那次,我想带琼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看威尔第的《唐·卡洛》,因为琼和我都很喜欢威尔第的这部剧,而且在琼生病以前看过好几次,所以就让我弟弟给我们买了两张很贵的票。但后来想想,我这个计划可能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在我们开车去纽约的那四个小时车程中,琼变得烦躁不安。当我在一个服务区停下准备给汽车加油的时候,琼说,她想去上厕所。我觉得她很难自己去上,但好在我找到了一位愿意陪着她去的老妇人。等回到车里后,琼开始变得坐立不安,非常暴躁。但当时,我还能够使她平静下来,并继续我们的旅程。我们的女儿安妮和我们待在一起,这让整个过程变得容易了许多。但在演出的时候,琼还是显得非常焦虑。第一幕刚开始,她就用平时说话的声音与我交谈,我们周围的人都朝着我们发出“嘘!”的声音,但她也完全无视。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想让她平静下来,并且压低了声音,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希望她能安静一些,坚持到中场休息。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带她出去,但这会儿正是咏叹调和合唱的段落,我不知道这会儿出去的话,该如何做到不惊动大家。我知道她有多爱音乐,也知道这次来听歌剧对她来说有多么特别。但坐在我们前排的人已经开始低声抱怨,甚至有一个人快速转过了身,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然后愤怒地说道:“能不能让她静静!”
好在我们最后还是撑到了中场休息,并没有发生什么其他事故。那时,我已经是惊慌失措、汗流浃背了。但从琼的脸上,我分明可以看出,这次能来纽约听到威尔第如此壮丽的音乐,她有多么兴奋。我尽力跟身边那些埋怨我妻子痴呆的人做出解释,可得到的还是他们的讥笑。“老年痴呆!”他们笑着说,“带她离开这里,她不应该来这里。”他们的无礼与冷漠让我忍不住想叱骂他们,但心里还是很矛盾。他们确实无情,但他们说的并没错,我确实不应该带琼来这里,我沮丧地想着。我不应该让她来听歌剧的,也不应该让其他人在听歌剧的时候被打扰。但她的脸上,分明洋溢着那么灿烂的欢乐啊!世界上最美的歌声会在后面几幕如约而至,我多么希望她能听到。难道身处疾病痛苦之中的她就不可以享受这种欢乐了吗?最后,我们还是留了下来,不管怎样还是看完了这场无与伦比的演出。但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握住她的手安慰她了,我担心她随时会变得紧张,进而陷入崩溃。当大厅里掌声响起的时候,我看着琼,琼也看着我,她脸上绽放着微笑,眼睛里则含着泪水。她对我说:“这演出很棒,对吧!”解脱与喜悦交织在一起,还混杂着某种胜利的感觉。但万一要是……想到这里,我也朝她笑了笑,亲了亲她的脸颊,紧紧地挽住了她的手臂,然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冲破涌动的人流,带她走出了剧场。
电影《柳暗花明》(2006)剧照,它讲述的是一对妻子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夫妇之间的故事
二、照护的核心:某种道义的互惠
有的时候,琼看起来好像很高兴,顶多会因为她自己脑海中虚构出来的某些对话,朝着谢拉(注:看护的名字)或者我发些脾气。是的,她有时候会听到某些声音,要么来自我们过去见过的人,要么来自某些她病态的大脑凭空制造出来的神秘人物。然后她就会在自己脑子里和这些声音对话。每次她生气时,都会用手打向谢拉或者我。但只消十到十五分钟,她就又会转怒为喜,朝我们微笑,甚至忘了她刚刚打过我们的事实。一直以来,琼看起来好像都认得我们是谁,也认得我们的孩子们。然而,在住院前大约半年时间,她却时不时会认错,甚至认不出我们。有时我们发现不了她其实没认出我们,因为她只是表现得有些困惑,或者只是有些不确定。毋庸置疑,家里所有人对这个问题都会觉得苦恼,但这种苦恼终究远不及她出现激越症状和攻击行为的时候。在关于痴呆症的海量文献之中,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失去私人记忆(包括那些关于至亲之人的记忆)的悲剧性,我也觉得这种情况确实是糟糕透顶。但对我来说,琼朝着我发脾气,或是表现出沮丧的情绪,要比她失去记忆更加麻烦,也更加难以对付。天哪,我们的处境得有多糟呢?面对这两种同样糟糕的情况,我现在居然要在其中挑出一个更好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日子算是过得比较顺利的。这些日子掩盖了琼已然很糟糕的病情,也延长了我的否认状态,我不想去面对转折点即将到来的现实。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段时间,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学术假。我的中国朋友都劝我把琼带到上海去——我在那儿有一个合作研究项目已经搁置好长时间了,他们跟我说,上海会有许多朋友可以帮忙照顾她。而且,在上海能得到的照顾,可能对于琼和我来说,要比我们留在波士顿更好。当我在考虑这一选择的时候,荷兰的一些朋友也给我发来了邀请,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晚些时候去那里做杰出客座教授的机会。对于这两个机会,琼都感到很兴奋,但我却很担心,我们是否真的能成行。我能把她平平安安地带到那里,再顺顺利利地带回来吗?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生活在国外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们征求了家人、朋友和医生的建议,最后决定出发,先飞到台北和香港,再飞往上海。短暂的台湾之行,将成为琼的一次告别,告别那些我们在1969 年就认识了的朋友和同事;也将成为一次庆祝,庆祝我们所做的近四十年的中国研究。
在洛杉矶机场的商务舱休息室等待登机的时候,我去餐厅给我们要了两杯咖啡。但当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眼前已是一团糟。我走开以后,琼很害怕,她不知道我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她自己在哪里。所以她站了起来,却撞上了玻璃茶几的锋利边缘,在她小腿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血溅得到处都是。服务生帮我清理了琼的伤口,并做了包扎。我们总算是赶上了航班,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在台北,在上海,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关注这个伤口的情况,需要去看医生,需要做小手术,还需要一天两次地清洗伤口、换药。我做了所有我需要做的事情,但实在感觉自己已经到极限了。好在有我们的中国朋友,他们轮流帮着我照顾琼,就像安妮、彼得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我在剑桥时也快要到极限了,是他们带我走出了低谷。我们在上海的时候,那些朋友给我们提供的支持丰富极了,有效极了,而且温暖极了,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而对于他们的支持,还能听懂一些中文的琼也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所以,诚如我的中国同事预言的那样,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成了我的某种喘息,比我们在家时要轻松多了。对我来说,这既反映出中国的朋友圈子对健康问题的殷切关照,也反映出我们的中国同事对于琼的爱。
后来,我们去了阿姆斯特丹,当时我们家里所有人都一块儿过去了。在那里,我们住在一家魅力十足的酒店里,边上就是阿姆斯特丹的一条内河。每周三次,琼和我会坐着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去莱顿讲课。但有一次下火车的时候,琼差点儿从火车和月台之间的缝隙掉下去,好在那时我已经养成了习惯,随时都会紧紧盯着琼,所以在她要掉下去的时候及时抓住了她。当时我非常震惊,可琼却似无事发生一样。然而,第二天的情况还要更糟。早上,琼醒过来——那是第一次,她没有认出我。我知道,这种事情早晚都要发生,可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措手不及。琼觉得,她床上躺了一个陌生人。她被吓坏了,开始尖叫着打我。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直尽可能温柔而又坚定地向她解释,我就是她丈夫——阿瑟,但她不管怎样就是不信我。她同意与我们的儿子共进早餐,但就是不肯让我接近她。她觉得,我是谁冒名顶替的,所以不可信。后来,到了白天晚些时候,她的症状有所改善,对于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甚至笑了起来。可我的心却碎了。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她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她的爱;可当她突然把我当作陌生人,并对我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能够站在医学的角度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从存在的角度来看,这就好像是我们之间的纽带——那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已经被锻造得牢不可破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绷断了。
在我们回到剑桥以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几次。有时候,她会再次变得非常偏执,觉得我是陌生人,取代了她丈夫,还想要杀死她。每一次毁灭性的症状发作,都暴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恐惧。但是,在发作结束以后,她却不愿再去谈论它们,甚至会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只留我在孤独与眩晕中盘桓,好像我也正在跌入琼所处的那个深渊。作为一名精神科大夫,我能够识别出患者的妄想症状,也很了解替身综合征——在这种综合征中,患者会出现妄想,觉得他们身边的人都是冒充的——但我却很少会想到这些症状对于患者家属的影响。现在,我对于他们的感受深有体会。
琼的症状在持续恶化。她开始出现尿失禁,不得不穿上成人纸尿裤。她还有三次出现了大便失禁,拉在了地板上。后来,我清理了这些烂摊子,也擦洗了地板,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大哭了起来,很确信自己很难再这样坚持下去了。琼一如往日,仍然在一边安慰我,给我加油打气。“你可以做到的!阿瑟,你可以做到的。”琼哀求道。于是我又这么去做了,做的还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多更多。
我的临床研究经验告诉我,不同的症状和行为问题,对于不同的照护者,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可能对于有些照护者来说,大便失禁并没有其他问题来得那么苦恼。然而,琼向来都非常优雅,非常矜持,在私人问题上也非常注重隐私。而现在,她生了这种病,发生了这种事情,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了。当然,这也可能反映出我自己对于排便控制问题的不适应——毕竟,我是精神科大夫,不是消化科大夫。其他家庭照护者也与我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的减退时,他们也曾感到非常崩溃。对于许多照护者来说,这就像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直到他们身患残疾的亲人——就像琼那样——坚持对他们说,他们可以做到,他们可以越过这堵墙。而让他们惊讶的是,他们真的做到了。然后,他们便会继续前进。这就是我想说的,照护的核心是某种道义互惠关系。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被照顾的那个人,在这种关系中也会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而在我们这里,正是琼,给了我继续前进所必须具备的动力。
2010 年夏天,我们经历了非常糟糕的几个星期。虽然琼已经开始服用好几种精神药物,她还是一刻不停地处在激越状态。每两天,她就会出现一次暴力行为:大声喊叫,拳打脚踢,极度兴奋。到了7 月4 日,我决定说,我们需要离开这里,琼也点头同意了。于是我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来到了我们位于缅因州的度假小屋,我们自从去年秋天起还没造访过这里。我让琼坐在一张舒适的扶手椅上,然后就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我们面前的河流,向她讲述天空和土地的颜色,还有参天枞树和断裂岩石的美丽。最后,我架起了烤架。那天是美国独立日,我烤了热狗和汉堡包,烤了玉米和西红柿,还在厨房热了一锅烤豆子。在屋外露台上享用这些美食的时候,我们俯瞰着远处的达马里斯科塔河——它似乎很平静,其实是缅因湾的河口,裹挟着不可预测的海的力量。就像大海会在一瞬间掀起滔天巨浪,给宜人的夏日带来疾风骤雨一般,此时此刻,琼的情绪状态也在经历着迅速的变化,并朝着坏的方向发展。
在我发现她这种变化之前,她就已经在害怕、惊恐与困惑中颤抖了起来。她忘了她人在哪里,也忘了我为什么要把她带到这里来。她开始出现某些近乎谵妄的症状,而此时,我的第六感也告诉我,某些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在琼彻底崩溃之前,我必须带她回家。于是,我收拾好行囊,关上了屋门。此时,我的胃绷得紧紧的,心脏也怦怦直跳。我一直在和琼说话,好让一切都看起来井然有序。然而,事情显然已经完全乱套了。我们上了车,琼开始来回拨弄她那边的车门把手,想要把车门打开。我担心,开车的时候她也会去这么开门,所以就一边用左手开车,一边用右手握住她的双手,搁在她大腿上,就这样开了三个半小时,直到深夜。当我们回到剑桥家中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束手无策了。
但回到家以后,琼就开始陷入疯狂。她剧烈地扭动着身体,砸烂了墙上的装裱画,又砸烂了好几只古董碟子。她变得极度偏执,高喊着我是陌生人,打算要伤害她。她躺在地板上,又是踢来踢去,又是大吼大叫。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但还是无济于事。我觉得相当无助,重重地坐到了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已经完全丧失了清醒思考或说话的能力。我甚至连眼泪都流不出来,只觉得自己很没用,想不出一点儿法子让情况有所好转。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堵无法翻越的高墙,我看不出自己该如何继续前进。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平息那些混乱,扫除那些绝望,只能任由它们吞没琼;我也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减轻我们面对那种悲凄的挫败感,终日沮丧。
当我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照护者分享这个故事时,他们总是回以一声悲伤的叹息,那是一种似曾相识,一种感同身受。关于照护者的那些心理崩溃和万念俱灰,我已经听到过太多相同的故事,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罢了。这些讲述照护者极限的故事,分明是一则则警世恒言。这些绝望的故事,都以相同的方式收尾,那就是照护者强撑着破碎而又疲惫的身子,又从绝望的谷底爬了上来,重新投入到照护工作中。当我想起神经科医生——那些每天都会碰到许多认知功能减退的患者的专家——的时候,我想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对于患者照护需求的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沉默寡言,是不是因为他们终究不愿去面对这种混杂了挫败与绝望的不安。
三、家庭照护与机构护理的艰难抉择
7 月4 日晚些时候,在琼躺在地板上睡着以后,我给我的一个同事去了个电话,想听听她的意见。她打算带上她的一个朋友一块儿过来,那个朋友是晚期痴呆患者精神科用药方面的专家。那天晚上在我家,他们和琼说了说话。琼当时已经醒了,虽然仍旧非常焦虑、害怕,但谢天谢地,她当时没有出现谵妄的症状。之后他们把我拉到了一边,跟我说,他们建议琼立即入院,去麦克莱恩医院的老年病房。他们说,在那里,琼的病情可以得到更好的评估,而且他们已经研发出了一套更为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方案,可以控制住她的激越和谵妄症状。
他们还告诉我,现在是时候好好找一家专门从事痴呆症照护的护理院来安置琼了。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躺在床上挨着我太太,感到非常挫败。我回想起几个月前,安妮、彼得和我也曾看过几家这样的辅助生活机构和护理院,担心可能有一天,琼的病情会严重到单靠我自己应付不了的程度。可是,我们看过以后就震惊得转身离开了,因为在我们去看的那几家中,绝大多数机构的条件都差得叫人无法接受。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要把琼送过去。可是,在经过了近十年的灾难之后,我的否认情绪已经越发强烈,我心里老是在想,我们可能还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才需要去面对这个可怕的选择。可如今,这一时刻即将到来。
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我们会拒绝接受要把琼送出去的事实呢?我记得,这种疑惑我此前也曾有过。有一次,我去波士顿一个绿树成荫的郊区,见一个非常不错的辅助生活项目的负责人。当时,那个负责人告诉我,在她看来,我把琼留在家里的时间太久了。她觉得,即使我那会儿想让琼进入她那个项目,琼的失能状况却已经严重到不再适合她们那种辅助生活服务了,琼需要的是护理院级别的照护。听了她的这番劝告,我很是恼火,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是说,她作为专家有权断定居家照护的时间是否过长或者过短。但如今,我重新思考了一下才发现,其实很多年以来,对于那些备选方案,比如辅助生活服务,我根本不曾多加考虑。
我把居家照护看作自己唯一的选择,觉得只要自己还能坚持,就会在家里照顾琼。过去一年(或者准确地说是过去十八个月),对于我和琼来说,都像是地狱。回过头看,我会发现,其实我们差点儿就没能挺过那段心惊胆战的岁月。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在更早的时间就想到辅助生活服务,但倘若我认定居家照护已经不再可能,认知照护服务想必是一个适合的选择。
我固执起来就像是一头犟驴,哪怕海枯石烂,我都要在家里照顾琼。我曾经如此许下过诺言,而琼也希望我能信守承诺。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但现实却远没有这么简单。经过近十年痴呆症的蹂躏,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曾经许下诺言的那个人了。而我作为照护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了。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我都已经筋疲力尽。而琼呢?好吧,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很难接受,我爱着的那个琼,我觉得亏欠许多的那个琼,已经不在了,已经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琼了。
我无法接受这种逻辑,因为我自己的承诺原本就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绝对的不合理。尽管这种承诺的基石同样也是爱情,但它能够维持下来却是因为某种负罪感。我敢肯定,当时的我是断然不可能这么去想的,因为我还没能理解到这个层次,或者说,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去想。那种内疚,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三十六年来,如果不是琼的照顾,我怎么可能好端端活到今天。虽然我给她带去了相当沉重的负担,可她却从未放弃过我。而如今,我才照顾她仅仅十年,怎么可以放弃她?如果就这样把她放弃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镜中的自己?去面对我的孩子?去面对我的母亲和弟弟?
在我犹豫不决是否要把琼送到麦克莱恩医院之前很久,安妮和彼得就已经认识到,有些事情必须采取不同做法了。他们发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他们知道,琼必须去护理院了,于是同我一起看了好几家这样的机构。可我为什么还是像头驴一样固执呢?在某个层面上,这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照护工作,已经养成了某种惯性,所以才不愿意改变。到最后,我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再这样坚持下去了,可我无论如何还是继续了下去。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我的固执也来自对于失败的非理性恐惧。我这辈子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执着,这既是我的优势,也成了我的软肋。我从不放弃,也从不允许自己半路退出。我表现得好像自己只要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就永远不会被打败,不论我或其他人需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然,早在认识琼之前,这种内疚感就已经与我如影随形了,可以一直追溯到我那个野蛮专横的童年时代。我想,在潜意识层面,这种心理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我生命中父亲的缺位。他是因为我才离开的吗?是因为我不值得他去爱吗?这些念头当然都是非理性的,可潜意识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照护,对于我而言,在其最深层的意义上,也就意味着救赎。照护拯救了我。我母亲不是曾经说过,照护让我变得更有人情味了吗?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不就是说,在那之前,我的人情味太少了吗?于是,当我允许自己出于自我保全的目的放弃在家里照顾琼的时候,所有这些心理层面的剖析,都重重地压在了我身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回,我们站在琼的立场上,只把我当作一个次要人物。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琼那时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无论我和我的家人怎么想,护理院都已经是她唯一的选择了。居家照护已经到头,其他方案也都是不可持续的。我将继续作为一分子参与琼的照护工作,但我无法再扮演中心角色了。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将既是一名参与者,也是一名观察者。这个悲凉的角色转换过程该如何描述,很多人都倍感纠结。但无论我们如何描述,它都是某种只能站在远处静静望着的照护,而在这里与那里之间,隔着机构,也隔着机构里的员工。所以,走了那么久,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这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我们来到了它的最后九个月。这九个月,既是阿尔茨海默病病程的结束,也是琼·克莱曼一生的结束。
注:
[1] 激越状态(agitation)是一种精神症状,表现为明显的坐立不安和过多的肢体活动,并伴有焦虑,程度可由轻至重,持续时间可由短至长,严重时会表现出兴奋冲动、威胁、攻击、自伤等行为。
[2] 违拗症状(negativity)是一种对他人的要求或指令表现出抵制或反抗的精神症状。
原作者|[英]凯博文
摘编|沈书枝
编辑|石延平
导语校对|王心
来源:新京报
希望我的绘本简洁又有力,像石头或贝壳
绘本《做玩偶的戈蒂》(Goldie the Dollmaker)首次出版于1969年,它像简洁到极致、仅由钢笔线条构成的画面一样,讲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
《做玩偶的戈蒂》首版书封,该书已由奇想国童书引进出版。
小女孩戈蒂的父母都去世了。她独自居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延续着父母的工作——制作木头人偶。和父母不一样的是,她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倾注了全部时间和感情,挑选材料,雕刻,上色。她制作的木偶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微笑,这也是她的木偶在商店格外受欢迎的原因。
“它们只是木头人偶而已。”
“我知道。但是我做了他们……所以对我来说,他们不仅仅是木偶。我必须爱他们。而且,对那些买了他们的小女孩来说,他们也不仅仅是木偶而已。”
《做玩偶的戈蒂》插图。(图源:奇想国童书)
有一天,戈蒂在销售她木偶的商店里,看见了一盏美丽的台灯。那是一盏来自中国的古董台灯。它太贵了,连店主都不认为会有人买它。而戈蒂看到它的第一眼,就无法忘记。它太美了。她用十八个木偶——制作他们需要花三个月时间——买下了它。朋友得知了灯的价格,说:
“你知道吗,戈蒂,我觉得,你可真是个艺术家。”
“为什么?”
“因为你疯了。”
戈蒂感到沮丧。当她独自待在工作室,看着小灯发出的微弱灯光时,她想:“我好孤单。”
夜里,那盏小灯在梦中对她说话了。
“戈蒂,我是做了这盏灯的人。”
“噢,它好美。”
“是的。因此,我们是朋友。”
戈蒂说:“可我并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我为你做了这盏小灯,无论你是谁。”
这是一个关于艺术家的故事,有关古往今来,艺术和人类的联结、艺术家如何创造、如何通过创造结交知音。
距离这本小书首次出版50多年后的现在,它和它的创作者玛丽莲·布鲁克·戈夫斯坦(Marilyn Brooke Goffstein,以下简称M.B.戈夫斯坦)几乎被遗忘——哪怕她曾凭另一本书《晚饭吃鱼》(Fish for Supper)获过1977年凯迪克奖章。
《晚饭吃鱼》首版书封,该书已由奇想国童书引进出版。
下文作者说,“若不是在日本一家书店偶然看见新近出版的M. B.戈夫斯坦的传记上由谷川俊太郎写的腰封: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你,但好像已经见到了你;若不是读完《做玩偶的戈蒂》深深感动后辗转各个书店与网站寻读她所有绘本,我不会记住M.B.戈夫斯坦的名字并知晓她的故事。现在,我也好希望M. B.戈夫斯坦会和我说:因此,我们是朋友。”
玛丽莲·布鲁克·戈夫斯坦(1940-2017)。
撰文 | 李茵豆
要花整整九个小时,
只为处理一根线条
工作是唯一真正的尊严,唯一真正的幸福。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他愿投身其中的事,那就是白活一场。我的选择是艺术。
——M.B.戈夫斯坦
1940年12月20日,戈夫斯坦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父亲上了战场,她在只有女性的家庭中度过了幼儿时期。战后,戈夫斯坦的父亲经营公司,从事广播电视相关的行业。每天晚餐后,他都会哼着歌,“脸上浮现一种温暖却遥远的神情,满脑子都是他的生意。”母亲是教师,每日去大学授课。父母努力工作的身影给戈夫斯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她认为工作真是最棒的事,人这一生一定要找到愿投身其中的事。
在中学时,戈夫斯坦的绘画才能已显露。1958年,戈夫斯坦高中毕业,离开家,去了位于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学习写作、诗歌与艺术。在那里,她开始尝试木雕和小幅的钢笔画,这些都最终奠定了她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她也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画画。
“我认为,重要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想做什么。大学时,我感到很惊讶,身边有才华的同学实在太多了。可是,与其跑来跑去地做很多很多事,不如花很长时间寻找、思考你真正想做的事。如果你找到了,并付出努力,那它一定会进步成长。”
戈夫斯坦大学时代的木雕作品。
1963年,大学毕业后的戈夫斯坦搬去纽约,在书店打着零工,希望成为一个插画师。她兜兜转转拜访各家出版社展示自己的作品,也在一些小书店举行了小小的画展,但始终未获得一个出版绘本的机会。
戈夫斯坦得以踏上绘本作家之路,该感谢一个童书界都知晓的人——莫里斯·桑达克。1965年,她在纽约办了一个小画展,桑达克来参观,并带来了他的编辑朋友迈克尔·迪卡普奥。在后者建议下,戈夫斯坦得以出版第一本书,《盖茨》(The Gats)。
迈克尔回忆,当时的戈夫斯坦是“一个有着闪闪发亮眼睛的年轻女孩,满怀激情地致力于以图画和文字构建自己的小小宇宙”。
《盖茨》,讲述了一群在树叶中生活的虚构小精灵“gats”的故事。
《盖茨》实拍图。
1966至1979年,戈夫斯坦投身绘本创作,每年出版至少一本绘本。它们大都以同样简单凝练的黑白线条画形式呈现。
她的另一位长期合作的编辑——也是她的经纪人和挚友——克罗尔提起工作中的戈夫斯坦,正如《做玩偶的戈蒂》中的小戈蒂一样,戈夫斯坦总是“努力又安静”地劳作。她会花整整九个小时,只为处理一根线条。“从我 1965 年第一次见到她开始,布鲁克·戈夫斯坦就从未改变过她作为艺术家、要按自己的意愿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决心。”
戈夫斯坦部分已出版作品。
戈夫斯坦曾说:“在我所有作品中,我想努力展示的最重要的事之一是,努力地工作、创造一些你觉得美好的、值得相信的东西,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美丽而值得尊敬啊。”
出版于1970年的《两个钢琴调音师》(Two Piano Tuners),也表现着这一主题。
《两个钢琴调音师》日版封面。
温斯托克是最好的钢琴调音师。他独自抚养着小孙女黛比。他带小黛比去参加音乐会,让她穿礼服,上钢琴课,演奏曲子,希望她能成为钢琴家。但小德比每日耳濡目染他的工作,只想穿裤子,拎着工具箱,成为钢琴调音师。
有一天,钢琴家立普曼来镇上演出。温斯托克为他调音。立普曼相信,全世界不会有人比温斯托克将这份工作做得更好。而小黛比偷偷去了另一位钢琴家佩尔曼夫人的家中,自作主张为她的钢琴调音……
“我想,她将来会成为一个蛮可爱的钢琴老师。”佩尔曼夫人说。
“如果不喜欢弹钢琴的人都不去教别人弹钢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钢琴家立普曼说,“每个人都有义务找到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想成为钢琴调音师。”小黛比说,“和我爷爷一样好的那种。”
“现在,你,立刻回家,换回你的礼服裙子,不要再试图给钢琴调音了!”温斯托克说。他对立普曼说:“当她听完你的演奏,受到感染,可能就会想成为一名钢琴家了。”
“可是,有什么能比让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更好呢?”钢琴家立普曼说。
小黛比很喜欢立普曼的演出,但这更令她坚定了自己要成为调音师的想法。正如调音师的工作区别于钢琴家,戈夫斯坦赞美的“工作”不仅是“艺术创造”,也是一种“匠人精神”。一个人找到一件平凡的小事,将它做到专业,并以此谋生,就是值得尊敬的幸福一生。
一间小小的房子,一个大大的花园,
一些朋友和很多很多书
18岁离家上大学前,戈夫斯坦生活在一个平静幸福的家庭。父母各自忙于工作,让她有了相对独立的思考和成长。“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童年时每天都在和家人野餐什么的,可能我会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让她获1977年凯迪克奖的《晚饭吃鱼》(Fish for Supper),是一本承载着和家人回忆的书。
这是一个简单又幸福的故事。“我”的奶奶早上五点钟起床,划小船去湖上钓鱼,钓很多很多鱼,天黑才回家。慢慢吃鱼,早早上床睡觉——这样,第二天,她又可以早上五点钟起床,划船去湖上钓鱼。日复一日,自在满足。
《晚饭吃鱼》插图。(图源:奇想国童书)
故事来自戈夫斯坦最珍贵的童年回忆——在明尼苏达州湖边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夏天。主角原型就是戈夫斯坦的奶奶。戈夫斯坦说,当奶奶一眼看到书中画面时,就开心地认了出来:“这就是我!这是我的帽子,这是我的裙子。”
尽管在家人的陪伴中长大,戈夫斯坦仍认为,她的绘本诞生于对“孤独”的体会。她从童年时就格外敏感,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生命,这种感受也成为她日后的创作来源。
在《做玩偶的戈蒂》里,戈蒂坚信每个玩偶都有灵魂。在《我的诺亚方舟》(My Noah’s Ark)中,小女孩将父亲为她雕刻的木头方舟视作陪伴一生的珍贵礼物,方舟上的动物都是她的伙伴,“像阳光一样温暖着我”。
《我和我的船长》封面。
在《我和我的船长》(Me and My Captain)中,玩偶小女孩望着窗边的木雕小船,相信里面住着一位船长。
“他会求我嫁给他。我会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晚餐。他会在桌下喂我的狗剩下的骨头。我们三个会过温馨的生活。但他是一位船长,总要远行。狗和我会待在家里,就像遇见他之前一样。但我们有了牵挂与等待的人,我们为他许愿,要有一个好天气。”
《我们的雪人》封面。
在《我们的雪人》(Our Snowman)中,小女孩和弟弟一起堆了一个雪人。晚餐时,她看着雪人孤独地站在渐暗的窗外,感到无比伤心,连甜点都吃不下了。
“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堆他啊。”
“如果你为了这种事儿就哭的话,”妈妈说,“你这辈子都会过得很难。”
堆雪人的情节并非来源于她的童年经历,但戈夫斯坦记得妈妈曾对自己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而她当时就哭了。
人或多或少总是孤独,又害怕孤独,于是将感情倾注于原本无生命的、不会动也不会变化的事物。
最能阐释戈夫斯坦对“爱”的理解的,也许是出版于1967年的早年作品,《布鲁奇和她的小羊》(Brookie and Her Lamb)。这本书在日本经由谷川俊太郎翻译、重版发行后,成为她最受当下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
《布鲁奇和她的小羊》外封和内封。
布鲁奇有一只小羊,她好爱她的小羊。可小羊什么都不会做。
她想让小羊唱歌,小羊只会咩啊咩啊咩啊。
她想让小羊读书,小羊也只会咩啊咩啊咩啊。
尽管这样,布鲁奇还是好爱她的小羊。
她给它做了温暖的小房子,挠挠它抱抱它,
小羊偎依在她的身边,咩啊咩啊咩啊。
《布鲁奇和她的小羊》实拍图。
“爱”,就是接受彼此的样子,自然地陪伴,没有要求,也没有改变,不是么?《布鲁奇和她的小羊》扉页,戈夫斯坦写着“给我的丈夫”。
戈夫斯坦的丈夫大卫·艾伦德是一家出版社的主编。他和戈夫斯坦一同生活数十年,是她工作的见证者,也是伙伴。他们一同居住在纽约郊外,屋外墙壁上雕刻着戈夫斯坦喜欢的话:
一间小小的/房子/一个大大的/花园/一些朋友/和很多很多书。
创造一些有力量又简洁的东西,
像一块石头,或一枚贝壳
贝类的壳不仅仅是它的房子,也是它的骨骼,是它用一生的时间形成的事物。我渐渐开始明白,我的书是一样的东西——是我的工作、我想要捍卫和保护的、在我死去之后将继续留存的。
——M.B.戈夫斯坦
1990年初,戈夫斯坦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停止出版任何自己的儿童绘本作品。哪怕合同还没到期,她也努力说服出版社放弃重印和发行自己的书。戈夫斯坦的丈夫大卫·艾伦德回忆说:“这是一个如此重要又不同寻常的决定,以至于很少人能真的理解。”
“这个国家的儿童出版业变了,不再有冒险精神、高尚品格、做决定的勇气。戈夫斯坦最开始很伤心,然后是愤怒,接着她意识到了,这已经不再是属于她的世界。她的创作是关于艺术、艺术家、对自然万物的珍惜之情。她不想被人说‘现在的小孩子都喜欢恐龙,所以你也要写点关于恐龙的东西……’。
戈夫斯坦一直认为,当你对一个孩子谈话,你是在对一个和你一样的人谈话。其他任何行为都是不诚实的。”
这或许是如今我们很难在书店读到她作品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属于她的世界。
对于“绘本”,戈夫斯坦有自己很顽固的理念。小时候,戈夫斯坦第一次读到绘本时,她以为,“这是上帝给的,而不是人类创造的”。她对着书中的角色喊,“快出来,快出来”。
“当我第一次知道书是人写的之后,我就想成为一个写书的人。那时我七岁或八岁。我不是内向的孩子,我也喜欢和朋友在一起,但,还是最喜欢书了。因为书实在太棒了……我的身边一直都有书,书中的主人公就像是陪我长大的家人。”
成为绘本作家后,她认为,自己在以一种仿佛“雕塑”的方式创作绘本,处理画面和文字。雕塑家以为,雕像原本就存在于木头和石头之中,他只是发现了ta,并将不需要的部分去掉。
“所有我书写的故事,原本都已存在于这个世界。我的工作只是接近它。我非常安静、有耐心地工作,而且从不放弃。”
“如果世上不存在绘本这种形式,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发明出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黑白色的、闪闪发光的小小剧场,我是作者、舞台经理、演员。”
“我对书写与绘画的理念是相同的:创造一些有力量又简洁的东西,像一块石头,或一枚贝壳。”
1985年,她创作了《我的编辑》(My Editor),送给克罗尔。在结尾,她写到“出版并不是奇迹,而是这个男人对‘那个我’的友谊——我自己都不了解、但很典型的‘那个我’:刚洗完澡、穿着格子衬衫、试图表现得聪明。”这本书为二人近二十年的合作画上了句点。
之后长达11年,M.B.戈夫斯坦在帕森斯设计学院任教。教学生如何创作儿童绘本,让她更清晰地理解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戈夫斯坦热爱中国古代诗人,尤其是白居易的作品——以最简洁的词句,表达清晰的意思。她教学生“不要在纸上画画,从纸上画画(don’t draw ON the paper,draw FROM the paper)”。
“是什么让你以为孩子们喜欢孩子气的东西?别教孩子如何成为一个孩子,他们想要长大。”
对戈夫斯坦而言,这是一段与创作截然不同的时光,似乎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但感觉幸福。“我真的很喜欢教书,这过程本身就像在写一本书。”
自1980年的《一位艺术家》(An Artist)开始,戈夫斯坦用蜡笔、水彩等工具创作绘本。它们都有着柔和美丽的色彩,讲述她关于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艺术创作的思考。
《一位艺术家》里的插图。
他想要用双手
塑造美
他尝试从自然中
创造秩序
他想要画出
脑海中的想法与感觉
艺术家就像是神
而神创造了他
戈夫斯坦说:“我喜欢写艺术家,艺术家是那些致力于比他们更伟大的事物的人。每一天对于他们都很重要。”1982年出版的《艺术家的生活》(Lives of the Artists)中,她介绍了伦勃朗、梵高、莫奈、马蒂斯、高更等等她热爱的艺术家。为了写这本书,她“读他们的传记,看他们的画作,直到感觉他们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1987年出版的《艺术家的助手们享受夜晚》(Artists’ helpers Enjoy the Evenings),艺术家休息以后,艺术家的助手——五支蜡笔们聊天、去咖啡馆、派对,甚至去纽约旅行。他们手牵着手在夜空中唱歌:我们又瘦又高,直到艺术家努力工作,使我们劳损。
放弃儿童绘本出版后,戈夫斯坦投身于植树与保护动物的工作,也用画作探讨人和自然、家园的联结。
M.B.戈夫斯坦在《姓名学校》(school of names)中的插画。M.B.戈夫斯坦在书中写道:“在我生活的这些年里,除了地球之外,没有其他地方是我的家。”
2017年12月20日,77岁生日这一天,长久患病的戈夫斯坦在医院去世,身边都是爱她的人。她对丈夫说,“照顾好我的工作还有猫”,并留下最后的诗:
我真的拥有了很好的一生
美妙的一生。
《做玩偶的戈蒂》最后一张插画。(图源:奇想国童书)
*2020年前后,经过数十年中断,在大卫·艾伦德以及编辑克罗尔的努力下,戈夫斯坦的部分作品得以重新印刷。在日本,出版社也精心重印了戈夫斯坦的部分作品,由谷川俊太郎翻译推介,使得新一代读者有机会认识她,并策划出版了她的传记画册。在中国,奇想国引进了她的两本杰作,由阿甲翻译,《做玩偶的戈蒂》和《晚饭吃鱼》。
——
参考书目:
1. Words Alone:Twenty-Six Books Without Pictures,M.B.Goffstein,DAVID ALLENDER PUBLISHER
2. ゴフスタイン:つつましく美しい絵本の世界,M.B.Goffstein,平凡社
3. 引用内容来自《ゴフスタイン:つつましく美しい絵本の世界》中2007年5月的采访。文中部分实拍图亦来自此书。
文/李茵豆
编辑/申婵
校对/柳宝庆
别把孤独当晚餐,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致当代年轻人
当代年轻人现状,早餐匆匆,午餐随便,晚餐可有可无。
周末,早餐不吃,午餐外卖,晚餐吃中午剩下的,或者凑满减买多的。
年轻一代的我们,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已背着买房买车的压力,恋爱可以谈,婚不敢轻易结。今年的新冠更是压得很多人喘不过气来,做什么都很难,不管是生意人还是打工人。
或许是使命,或许是理想,让许多人孤独地生活在城市,下班的时候,万家灯火,没有一盏灯是为你点亮,这个城市的繁华,终究与你无关。
累了一天了吧?别把孤独当晚餐,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外卖从哪里取到的,只有外卖小哥知道,也许是装修雅致的餐厅,也许是只有一间房的小作坊,但是他们都很忙,没空为你做健康又精致的饭菜,短短几分钟的出餐时间,他们为你准备的,都是重油、重盐的食物。
一个人吃外卖,也是孤独的,于是你匆匆解决,想逃避这种孤独感。
有时候下班回家,想自己做,但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一个人的晚餐,何必大费周章?
亲爱的年轻人,其实你做的饭很好吃呀!你不必像一个美食博主一样拥有各种餐具厨具,也不必像一个大厨一样做出满汉全席。
你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冰箱,一个炒锅,一个煎锅,一个煮汤的锅,一个电饭煲。在周末的时候去市场淘一些你喜欢的文艺的盘子和碗。
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不那么顺利,做一顿饭需要很长时间,慢慢就好了,你要相信。
精美的盘子里,放着你精心切好的水果,透明的玻璃杯里装着温热的牛奶,一个丑丑的煎蛋,一块全麦面包,一份自制的意面,一份你煎得或生或熟的牛排,它们也可以凑成一份营养美味又健康的晚餐。
在不加班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孤独的,一本烹饪的书籍,菜谱,美食博主的小视频,菜市场挑选的一颗香葱,一把香菜,几个鸡腿,一朵西蓝花,几朵香菇,一小把小白菜,都可以做你喜欢的饭。
放松自己,烹饪也是一种乐趣。在你精心为自己准备一份精致的晚餐的时候,孤独已经被驱散,吃着自己做的食物,心里甜甜的,乐开了花儿,快乐能让你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对身体也健康。
别把孤独当晚餐,要与健康为伴。生活再苦,寻找微笑里的甜。
我是GiHOME,关注你的健康生活,更关心你!